这……这里究竟……
正是疑惑,正是怔愕,昆仑山的典藏楼的内室里为何有如此多的白骨,且去仔细一看,竟是片缕不沾,只剩下嶙峋枯骨。最新地址发送任意邮件到 ltx Sba@gmail.ㄈòМ 获取并且完全没有正常的尸骨那样,带着灰暗之色,它们皆是一片洁白如雪,似乎完全未曾经经历腐朽的过程。
并且,这些骨 ,并非全是
,并非全是 类之骨。有的
类之骨。有的 骨边上遗落着犄角,有的似乎是牛,有的似乎是象,还有一些
骨边上遗落着犄角,有的似乎是牛,有的似乎是象,还有一些 骨只能看得出不是
骨只能看得出不是 类,却分辨不出属于什么……很杂,很多。
类,却分辨不出属于什么……很杂,很多。
不过有一点很意外,通常无论是什么尸骨,看起来都令 心中生寒,但是这些却正如它们的色泽白,不论是看多久,心中都是空白,对它们丝毫没有生起半分寒意,不知怎的,有一种它们被净化过的感觉。
心中生寒,但是这些却正如它们的色泽白,不论是看多久,心中都是空白,对它们丝毫没有生起半分寒意,不知怎的,有一种它们被净化过的感觉。
当岔完注意力回过来时,他乍然发现,方才无意中踢到的那一脚,将一些白骨踢散了一些,于它们之下,露出了一些类似于文字的边角笔画,像是掩盖了什么字迹!
以前闲来无事总看闲书时,常有写到一些尸体底下隐藏着重要的功法与心法的秘诀,莫非这里也是?
抑或者,是死者留下里什么指示?!
林苏青顿时感到后背一阵寒意顺着脊梁骨直抵尾椎,紧张与惶恐戛然袭来。他曾经处于好冒过许多险,有些甚至差点丢了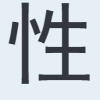 命。所以此时……
命。所以此时……
伸出去的手跃跃欲试,却又犹犹豫豫地踟蹰着收了一回又探出一回。思来想去,他 脆一咬牙吞咽下疯也似的分泌的唾
脆一咬牙吞咽下疯也似的分泌的唾 罢了,
罢了, 都已经在这里了,如若不得不死,就是逃也无法可逃,倒不如既来之则安之。
都已经在这里了,如若不得不死,就是逃也无法可逃,倒不如既来之则安之。
于是,他屏起呼吸凝住了,但并不用手去推,而是改用脚尖去将那些掩盖着字迹的白骨往边上踢开了去。
亡者之灵无论是在还是已经离散,都不便惊扰,本来用脚去踢就已然失礼,所以他更不能一脚将它们踹开,做成极为不尊敬,可是心里又些害怕实在不敢下手去挪,于是,他在心里对这些枯骨道了一声歉意,便轻缓地以脚尖去一点一点的推开。
先看到的是一个“矢”字,蚕 燕尾,是隶书的着笔。前面的骨
燕尾,是隶书的着笔。前面的骨 往后里便与后面的骨
往后里便与后面的骨 堆在一起,不大好推开,他稍微多用了些力气“知足”。
堆在一起,不大好推开,他稍微多用了些力气“知足”。
是凿在地面的,在白玉石地面上造出的小字,不是如他方才那样刻意仔细去看,实在是难以发现。
可是为什么,为什么会在右侧的桌脚边上特地凿出“知足”二字呢?这间内室里又为何有如此众多的白骨呢?
难道“他们”都是通过白泽尊所赠的白玉壁而来的?
林苏青顿时怛然,膝下一软,跌坐在椅子上,他脑子里突然闪出无数种猜测。难道是白泽尊故意诓 进来,却是有来无回?难道是这里有什么隐藏的危险?可是为何会在什么也没有的屋子里,凿下“知足”二字呢?
进来,却是有来无回?难道是这里有什么隐藏的危险?可是为何会在什么也没有的屋子里,凿下“知足”二字呢?
他登时联想到这里是典藏楼,收藏着无数的典籍,莫非用意是警示进 者要求而知足?
者要求而知足?
所以这些尸骨皆是因为不知足而亡?
可是既然有死亡,那么这里必然是暗藏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,至少他现在还没有看见,而那“东西”能够在一瞬间取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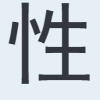 命,甚至连衣物、血
命,甚至连衣物、血 半点都不留下,只留下白骨。
半点都不留下,只留下白骨。
那他呢?等待着他的结局是什么?
林苏青强迫自己冷静下来,要迅速冷静下来,慌不得,要冷静。
而此时盘坐于小木屋中大作的他的本体,也正随着心境的变化而呼吸急促,一 的冷汗,捏的手诀方才还掌心发胀发热,此时亦是满手心都是冷汗。
的冷汗,捏的手诀方才还掌心发胀发热,此时亦是满手心都是冷汗。
静,一定要静下来,必须要静下来。
必须先抛开一切,先恢复冷静。世间本无无,万般皆妄想。冷静。
昆仑山典藏楼的白玉内室之中的林苏青的意识,此时仍是一脸惊愕地坐着,他是来学习如何考上三清墟的,是要走那个特例。知足……知足的话,那么,学完即走,再也不来,算不算知足?
如是一想,桌子突然没来由地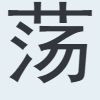 起许多金屑,如同积累许久的灰尘,猛地一拍桌面,将他们统统震起,它们金光闪闪,吸引回林苏青的注意,旋即它们汇聚成了两枚金字,依然是蚕
起许多金屑,如同积累许久的灰尘,猛地一拍桌面,将他们统统震起,它们金光闪闪,吸引回林苏青的注意,旋即它们汇聚成了两枚金字,依然是蚕 燕尾的隶书,圆润平滑恰不见一丝锋锐求得。
燕尾的隶书,圆润平滑恰不见一丝锋锐求得。
求与得之间有着超过一个字的空隙,林苏青不确定是自己多想了,还是的确是他所想的意思,这可能是两个字,意味着两个动作,一谓求,一谓得,有求便可得。
但也可能是一个词,意味着结果。
林苏青研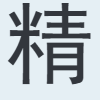 竭虑,联系着那些白骨,联系着“知足”二字,联系着白泽尊曾经说过的所有的话,脑子里
竭虑,联系着那些白骨,联系着“知足”二字,联系着白泽尊曾经说过的所有的话,脑子里
 糟糟,所罗列的因果打
糟糟,所罗列的因果打 了重列,重列之后又打
了重列,重列之后又打 。
。
白泽尊说能帮他考上三清墟,然后便说里昆仑山的典藏楼,也就是说只要是在这里,他便能寻到方法。
知足,学到方法便走。
乍然,桌子两边实心接地面的地方,桌面突然凹陷下去,惊得林苏青心惊 跳,霎时凹下去的部分又迅速恢复,而恢复时桌面上竟是堆叠着成千上百本书籍。
跳,霎时凹下去的部分又迅速恢复,而恢复时桌面上竟是堆叠着成千上百本书籍。
随即,“求得”二枚金色猛地化作一阵金雾消散。
他懂了。他居然想对了。
那么这些书里所记载的,应当就是考三清墟需要掌握的内容吧!心里陡然慌了起来,不是害怕的慌张,是一种激动、兴奋的紧张,心弦猛地紧绷,遽然浑身发抖。
他调整了心境,伸手去触摸那些书籍,触手冰冷,像是刚从冰窟中取出来似的。他将堆垒在一起的一摞摞书,取下几本大致,看了一些书名,或翻了几页内容。
其中有保存完好的竹简,有以针线装订成册的缯书,还有以 壳、石
壳、石 刻字的,它们被分别以绳线捆绑,每一堆大约就是完整的“一本书”,等等等等,许许多多,各式各样。
刻字的,它们被分别以绳线捆绑,每一堆大约就是完整的“一本书”,等等等等,许许多多,各式各样。
而这些典籍,并非全是从未见过的生僻古书,其实博古贯今,大有一些而今也尚在流传的名书。就是林苏青这样的普通读书 ,虽然没有仔细去拜读过,但也都有所耳闻。
,虽然没有仔细去拜读过,但也都有所耳闻。
譬如《易经》,这是多么传统且经典的一部作品。不过,这里的《易经》确实记载于许多块巨大的卜骨之上的,所使用的全是甲骨文。
他当然识得甲骨文,他自幼学习书法,接触过许多字体,除开常见易辨别的字体,诸如石文、陶文、兽皮文、钟鼎文、竹简文、绢帛文、木牍等等他自幼时起便皆是有过接触,尽管有些已经忘记不大会写了,但仍然能够边猜边认个八九不离十。
何况甲骨文是他的老师着重教授的字体,特地强调不会写也必须能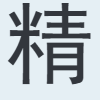 准的辨认。大抵是由于对于林苏青那边的世界来说,甲骨文上承绘图刻符,下启青铜铭文,算是最早起的成熟字体,在文字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。
准的辨认。大抵是由于对于林苏青那边的世界来说,甲骨文上承绘图刻符,下启青铜铭文,算是最早起的成熟字体,在文字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。
然而,它作为最早期的字体,却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消失了两千余年,并且因它的莫名消失,导致了许多文化的断代。
不过,值得一提的是,甲骨文于他那边的世界,距他离开时,所发掘的大约有五千来字,但被研究者们成功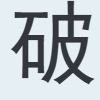 解识出涵义的尚不足两千字,最多也才一千五六百,尚有三千余字未被识出涵义。
解识出涵义的尚不足两千字,最多也才一千五六百,尚有三千余字未被识出涵义。
但,唯独他的老师能识得全部甲骨文,至少在他有限的认知里是的,至少当时的世面上所有有关于甲骨文的报道,都仅仅停留在识别不到两千字。
他也不知老师所言是真是假,总之是被迫作为学业,不得不跟随老师学了个齐全,当然,也是老师所谓的“齐全”